簡介志文出版社新潮叢書等500本 (1/5 。1967年的岩波 Anderson童話書...... ) 周二26日周三27日(約11點)將由曹永洋,鍾漢清直播,詳細介紹新潮文庫數百本書各類要目和譯者。《張清吉紀念文集》討論,數十位讀者的心得和展望。周四二十八日新書發表會。書出版了,感謝曹永洋、廖志峰兩先生。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342178548200668
////
簡介志文出版社新潮叢書等 (2/5) : 台灣多彩多樣的出版生態: 至70年代末 (1980),新潮叢書已出版約250本,參考《張清吉紀念文集》(2023)末篇附錄書目 ;中國時報,以鹿橋《人子》(遠景出版);聯合報系,以吳念真《抓住一個春天》(1977)50年後新版感言,感人的故事。(聯合副刊的馬主編,遠流出版的老闆,周遭的親友和社會史詩……當年,給年輕人關心,陪養,機會等,都很了不起。請讀末段。)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818194153419297
簡介新潮叢書等志出版社500本 (2/5 ) 台灣多彩多樣的出版生態: 至70年代末 (1980),新潮叢書已出版約250本,參考《張清吉紀念文集》(2023)末篇附錄書目。吳念真《抓住一個春天》(1977)50年後新版感言,感人的故事。
二。系統中有人。吳念真的故事感人深,你可了解
好像也只有在那麼單純而美好的年代裡才會有這麼一群長輩,他們扒鬆了泥土,開闢了一塊園地,讓不同的種子自在地落下、萌芽,他們殷勤澆灌、施肥,然後微笑地看著他們各自成長,長成他們各自喜歡的姿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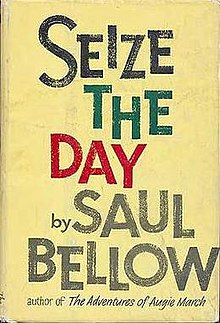 First edition | |
| Author | Saul Bellow |
|---|---|
| Country | United States |
| Language | English |
| Publisher | Viking |
Publication date | November 15, 1956[1] |
讀吳念真《抓住一個春天》(1977)50年後新版感言,對照林將軍“上海支付寶的一天”(2023年九月林公孚;林中斌 2017.6.7)
吳念真(1952年8月5日—),本名吳文欽,筆名念真,臺灣影視導演、編劇、演員、作家、廣告人、作詞人及藝術監督。1952年8月出生於新北市瑞芳區猴硐大粗坑(九份附近)[2][3],父親入贅,身為長子的吳念真,過繼母系,從母親的家姓[4]。現任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董事之一,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名譽理事長[5]。是首位三金(金馬獎、金曲獎、金鐘獎)全滿貫得主。
| 吳念真 | |
|---|---|
 | |
| 男藝人 |
| 1977年 | 《抓住一個春天》 | 聯經出版,臺北 |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Hamilton,各國名寓言集(伊索……);羅馬帝國衰亡史Gibbon吉本。網路資訊 音樂系列,
------
昨天終於拿到書了。
回想出版過程也是一次不可思議的旅程。
2018年9月28日張清吉先生過世,
思想坦克晏山農約稿談新潮文庫對我的意義,
義不容辭。
後來老曹有意出版張清吉先生的紀念文集,
想收錄思想坦克上的文章,
請我聯絡晏山農,
阿達一口就答應了,
非常爽快,
我也同時向老曹表明出版這本文集的意願,
我應該是我們這輩出版人少數親見過張先生的人,
責無旁貸。
意外地,
2022年12月底,
賴其萬醫師突然來訊說要贊助出版經費,
我並沒有開口,
於是,很快地敲定張先生的忌日為出版日期,
總共有十人贊助,
連同老曹、鍾漢清。
十分感謝🙏。
張先生的過世日期是9月28日,
還有什麼比這更有意義呢?
教師節,
也是新潮文庫日,
是文化日,
也是啟蒙日。
沒有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
沒有讀過新潮文庫的人,
也枉為文青。
謝謝張清吉先生。
謝謝所有的前輩文化推手,
讓我成為今天的我,
新潮文庫佔首功。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在雄獅星空的新書發表會歡迎各位朋友的光臨。
廖運範院士會開場致辭,
細說因緣。
親愛的朋友,
我們下星期四雄獅星空見。
#謝謝所有協力出版的朋友衷心感謝🙏。
。。。
《張清吉紀念文集》出版了,感謝曹永洋、廖志峰兩先生。10月份《台灣星空網路季刊》再出發(物換星移....) 9月份BLOG 的文章,或許可回顧、展望
- 張己任:十方 盤帶欣賞會,兩人(校友)合作 各家第九交響結束後持續
- 2023 羅馬帝國衰亡史 Edward Gibbon’s THE DECLINE AND FALL ...
- 出版《張清吉紀念文集》吳鳴的《秋光拾得》......高分子改善水泥 林世堂
- 禁書……劉大任 《紅土印象》;顏元叔《文學經驗》《行走的樹》
- 藝術家 (581期 2023.10 )目錄。 典藏藝術
- 《張清吉紀念文集》發表會九月二十八。 曹先生交的手稿(徐復觀給王孝廉)2023年9月9日。 一本書...
- 鍾肇政:《史懷哲傳》Albert Schweitzer 《文明的故事》《歌德自傳》《名著的故事》《名...
- 新潮文庫《100個偉大音樂家 》(1981) 《巴洛克音樂 》
- 沙特在新潮文庫、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
- 《張清吉紀念文集》2023 發表會訂於9月28日下午三時, 在雄獅星空,《新潮文庫》張清吉(19...
- 劉克襄(岳人)談芥川 富士山
- 1967年2封
- 徐復觀先生給王孝廉的書簡謄錄(曹永洋)稿子交鍾君
《張清吉紀念文集》發表會九月二十八。 曹先生交的手稿(徐復觀給王孝廉)2023年9月9日。 一本書的故事,2022年聖誕節前,曹老師路過寒舍小聊有感2022.12.24
廖志峰──在 Link Lion 雄獅星空。
https://hcbookstory.blogspot.com/
漢清書話:從「新潮文庫」說起 The Story of Some Books
是祝福華為,抑或詛咒?
昨天是孟晚舟獲釋回国兩周年,也是華為發布新產品的好日子。今日多個黨媒皆喜氣洋洋地報道,有中国網民自掏腰包,在紐約時代廣場的戶外巨型螢光幕上,播放孟晚舟手持鮮花返国的相片。這樣爱国的義舉本來令人感動,但當我看到上面的英文字幕,就感到有點不祥。
螢光幕的英文字幕,寫有「The light boat has crossed the mountains」(是李白名句「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英譯)、「be far ahead」(遙遙領先)等字句。該網民嘗試解釋,說:「華為,打破了美國科技封鎖,在9月25日開發布會,輕舟已過萬重山!遙遙領先!」
一般來說,「cross the mountains」的主語是人、馬、車等陸行動物或交通工具;以船為主語也不是錯,因為你可經水路在山下橫過,故「cross the mountains by boat」也是有人講的,只是比較少見。當然,你也可按字面理解為「一艘船在山上移動」,如荷索1982年電影《Fitzcarraldo》其中一幕,正是把一隻船拉上山。
要是你懂得的中文詞彙夠豐富,看到「The light boat has crossed the mountains」一句話時,其實很難不聯想到以下兩個成語(我懷疑今天大多數中国人都不懂)。
一是「推舟於陸」,比喻徒勞無功,出自《莊子.天運》:「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意思是:「如今想在魯國推行周的制度,就像在陸地上推船,徒勞無功,自身也必有禍殃。」「推舟於陸」一語,今天少見人用,我們日常多數講「拉牛上樹」。
二是「罔水行舟」,即無水而行舟,比喻行為顛三倒四、有乖常理,出自《尚書.益稷》:「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這是禹告誡帝舜的話,提醒他勿像堯的不肖子丹朱般,「沒有水而在陸地上行船,還在家聚集了一群無賴,只顧淫樂,終於敗了父子相傳的帝業。」
今日華為,在外要面對全球多國的科技制裁,在內要配合總加速師的英明領導,就算有「非凡大師」填海華做代言,這隻死雞要撐下去恐怕也是「推舟於陸」。光是生存已這麼難了,還反過來自high大喊「遙遙領先」,不是「罔水行舟」又是什麼?相比起「輕舟已過萬重山」,我聯想到的兩個成語,似乎更適合形容現在的華為。
順帶一提,李白詩有很多更好譯法,實不必逐字譯為「The light boat has crossed the mountains」。以「過」字為例,譯成「glided past」、「glided away」、「sailed past」等,都可免卻「山上行舟」的不祥聯想。至於「輕舟已過萬重山」全句,專門翻譯詩詞的許淵沖曾譯作「My skiff has left ten thousand mountains far away」,比中国網民的「祝福」達意得多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請訂閱支持十三維度Patreon:
https://www.patreon.com/sefirot
再版自序
面對這本書,一如面對青春、面對初戀,或面對初為人父的自己,雖然,它的年紀比起兒子都要大上許多。
《抓住一個春天》是我人生的第一本書,出版當年我應該二十五歲左右吧?而今年七十一,四十六年過去了,從少壯到古稀。
遺忘,彷彿是年歲增長後的必然,就像年輕的時候曾經聽過的一首歌的歌詞所說的:「……若我不能遺忘,這纖小軀體又怎能載得起如許沉重憂傷?」所以,若非重新翻閱,大多數的篇章都早已面貌模糊,唯獨作為書名的這一篇始終歷久彌新,然而,記得的並非文字內容,而是從書寫、投稿、發表直到出書前後所遇到的人與事,因為這些人與事幾乎影響、改變甚至決定了我之後的生涯。
人老話多,文長慎入,有興趣的就請耐著性子聽我慢慢說。
一九七五年是我三年兵役的最後一年,年初,部隊剛從金門移防苗栗大坪頂,沒想到當環境的整理整頓、防務的部署調配剛完成,部隊才稍微放鬆下來開始正常輪休時,老的那個蔣總統卻就在那個時候過世了!
部隊再度進入長達一兩個月的一級戰備,休假取消、電影院關門、電視變黑白……除了睡覺之外全員全副武裝,政治課上不完,下課時間廁所外到處都堆著暫時脫卸下來的鋼盔,和掛著子彈袋、醫護包、刺刀、水壺等等的沉重的S腰帶。有一天,營長要進來尿尿,幾乎找不到落腳處,氣得在外頭大罵:敵人不要多,只要一個帶把步槍來攻廁所,半個部隊全光著屁股被押走!有個阿兵在裡頭低聲回應:不會啦,營長會帶著他的短槍來救我!
也許是白天的政治課睡太飽,阿兵們夜裡精神似乎特別好,有一天當我輪值午夜十一點到一點的安全士官時,發現中山室裡平常乏人問津的文康書箱中竟然只剩幾本像《蘇俄在中國》之類的磚頭書,那些比較容易入口的武俠小說和教忠、教孝培養愛國情操的小說全部被借走了!長夜難度又苦無消磨方式,正當懊惱不已的時候,我們的預官輔導長正好從他房間出來,問我在找什麼?我說:沒書看!他說女朋友給他寄了一些書來,有一本小說他剛看完,「夭壽好看,你一定喜歡!」他回房把書拿出來給我,說:「慢慢看。」
那本書的封面很不一樣,很新潮、很醒目,書名只有一個字:《鑼》,作者是黃春明。
書不厚,真的夭壽好看,所以要慢慢看真的很難,整本看完時,才發現我連一點到三點的安全士官都忘了去叫交班。既然如此,那就乾脆從頭再看一遍。
清晨,起床號響起之前,輔導長拿著盥洗用具走出房門,看到我只愣了一下,說:看整夜?我笑了笑點點頭,他說:我就知道你會喜歡,因為裡頭有一個主角的名字跟你一樣,叫「憨欽」!此外,他什麼都沒說。
《鑼》和黃春明先生在那個夜裡啟發我的是:只要多看一眼、多聽一下,身邊再平凡的人都有故事,都會是一本書。
後來,我買了一本筆記簿,把小時候記得的事、鄰居或兵士們講過的故事逐一條列,覺得內容逐漸長大,大到差不多了、自覺很完整了,就寫下來往部隊有訂閱的報紙副刊寄。結局你應該想也知道,每寄每退,但或許年輕,心理自衛機轉很強大,退得快的會有短時間的失落,只要退得慢一點的,就會想說:應該寫得還不壞,所以他們才會猶豫吧?
部隊輔導長是可以檢查信件的,所以我寫的稿子他幾乎每篇都會看過,而每次把退稿拿給我的時候都會說:加油哦,還有進步的空間!或者:這篇我都看不懂你要表達什麼呢!
不久之後他就退伍出國念書了,新的輔導長是職業軍人,第一次拿到報社的退稿時,把我叫進房間,念了一兩個小時,其實只是傳達了一個重點:退伍之後,你要寫什麼我管不著,但只要還在部隊,就別跟報社有關聯!
我是聽話的兵,從此只有筆記、日記,沒有投稿。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我退伍了。
十五歲初中畢業後就到台北工作,雖然之後也半工半讀念完高中補校,但其實身無一技之長,所以退伍前已經決定了兩件事:第一,先找到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第二,考夜間部大學,因為對當時做學徒已經太老的我來說,念大學應該是取得「專長證明」最快速的途徑。
於是,一九七六年初,我進了台北市立療養院(現在的台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當雇員。
工作有著落之後,開始進行第二個計畫。首先去南陽街的補習班了解一下夜間部大學到底有哪些科系?要考些什麼科目?還有,離開學校三、四年了,課本內容是不是有什麼改變?
不問還好,一問之下整個人就涼了半截,因為除了歷史、地理和三民主義勉強還有點記憶之外,國文、英文、數學幾乎和先前所讀的完全不一樣,尤其是數學,根本就像天書!當時已經是二月,而夜間部聯招是八月初考試,也就是說我只有半年的時間必須去消化一卡車近乎全新的教科書,連補習班的人都說:「是有難度,但未必不可能,而且你剛退伍,錄取分數有降低百分之十的優待。」然後給了我一堆參考講義和五節免費試聽。
由於我要上班,所以那五節試聽我打算用一個星期天全部用完。
那天北台灣難得豔陽高照,陽光驅走多日來的濕冷,火車站前紅男綠女熙熙攘攘,個個笑容燦爛,而才一街之隔的教室裡卻寒氣未散,燈光昏沉。應該小我四五歲左右的男孩女孩一個個面無表情、鬱鬱寡歡,老師拼命講笑話,他們似乎也不太領情,我鄰座的一個男孩甚至還說:拜託!這個月我已經聽過四次了!
午休的時候課堂裡只剩下少數幾個人,三、四個男生正圍著兩個女生攪和,主題是想說服她們下午蹺課,一起去陽明山郊遊,說:「多上下午這幾堂課也不一定能多考幾分,沒去曬曬今天的太陽絕對卻會遺憾一輩子!」
然而下午的課程一開始,我發現那幾個人都還在,依然面無表情地看著老師,鬱鬱寡歡。
黃昏回到醫院宿舍,回想這一天的上課情形,發現這樣的課程其實並不適合我這種狀況的學生,我應該放棄一兩個可能徒勞無功的科目,把有限的時間集中在「有讀有保庇」的學科上。於是立定主意:數學放棄!英文、國文靠實力,三民主義死背,歷史、地理集中力氣!
然而歷史地理總共十二本,光要看完都不容易,哪有「精讀」的餘裕?沒想到補習班給的簡介資料上剛好有一則「用地圖讀地理、歷史」的廣告,號稱只要買四本地圖就可以讀通十二本地理、歷史,好極了!這麼一來我好像連課本都可以不用買啦!
也許心裡的壓力得到一點點緩解吧,當我吃著晚餐時忽然想起相約要蹺課的那幾個男孩,想說:如果一大早的陽光就引誘著他們逃離教室,而且也順利說服幾個女生結伴相隨,那今天應該是無比歡樂的記憶吧?當然也會想到:是什麼樣的父母和家庭可以理解和接受孩子們這種暫時「短路」的行為?
想著想著,畫面就出來了,於是拿出筆記本開始打草稿,想像著那幾張年輕的臉孔,模擬著他們的語氣,想著白天戶外的光影和溫度,想著他們這一天裡可能遇到的良善的人……就這樣把自己當成一個旁觀者,看著他們開心的這一天,一路跟著記錄下來。過程中好像沒有什麼停歇,只記得燒了一次開水,還有夜裡溫度又降了,找了襪子穿上繼續寫,然後寫完,抬頭時才發現天已經濛濛亮。
沒多久,好像才三月初,《聯合副刊》就登出了這篇文章,沒錯,就是〈抓住一個春天〉。也許因為太長了,還分上下兩天登完。記得那天的日記裡,我寫了這樣的一句話:「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可以臉不紅氣不喘地跟人家說:明天,報紙上將會有我的文章。」
文章發表後的某一天,接到報社寄來的一封信,很薄,絕對不是退稿,打開,是一張便箋,很秀氣的字,寫著:念真兄,請多賜短篇。祝筆健 馬各。
夜裡,我問隔壁宿舍一個也經常投稿的醫生說:馬各是誰?他說:好像是《聯合副刊》的主編!
馬各先生或許都不知道他這封短信的威力,他讓這個剛退伍的年輕人幾乎忘了要考大學這件事,每天一下班就在宿舍裡寫寫寫,因為他單純地覺得既然不知道該如何回信表示謝意,那最好的方式無非就是「再寄短篇」。
六月,當副刊登出我第三篇小說時,宿舍裡的同事們終於受不了了,說:你到底要不要考大學啊?
而就在決定暫時收心,好好念書之後沒多久,有一天樓下警衛忽然喊我的名字,說有找我的訪客。下得樓來,發現是兩個年紀看起來沒大我多少的人,身邊是一部舊舊的摩托車。他們分別自我介紹,一位是政大教授吳靜吉、另一位則是遠流出版社的王榮文。前者當時比較陌生,至於後者那陣子倒是經常耳聞,因為他的出版社剛出版了一本驚動萬教的小說──吳祥輝的《拒絕聯考的小子》。
他們說:在《聯合副刊》上連續看到我幾篇創作,很有潛力,很希望有機會出版你人生的第一本書。
沒多久之後便接到王先生寄來的兩張出版合約和一封信,他說這份合約並不具有任何法律約束力,只是彼此的約定、承諾和期待。
我簽了,因為對我來說那是一種被注目、被肯定的溫暖和鼓舞,一如馬各先生的便箋,短,卻強大無比。
八月,大學夜間部放榜,考上輔仁大學會計系。取代十二本課本的那四本地圖效果真的不壞,拿到可以接受的成績。原本就決定放棄的數學只看得懂三題,對兩題錯一題,倒扣之後實得10.18分,這被宿舍裡幾個台大醫科畢業的醫生笑了好久,常開玩笑說:這樣的數學實力去念會計,以後你做的帳誰相信啊?
不久之後《聯合報》決定舉辦文學獎,有一天馬各先生約了好多年輕作家在報社聚會,那是我第一次和他見面。他說一直以為我應該是年紀稍微大一點的醫護人員,沒想到卻只是一個剛考上大學的「小孩」啊!
也許他真的把我們幾個年輕的創作者都當「小孩」吧,老怕我們餓著了,所以常約我們去他家吃飯、聊天。
一直記得他家的樣子,和駱太太燒的菜。有一回她炒了一道青菜,樣子看起來是韭菜花,但味道卻不是,忍不住問了,才知道那叫「蒜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樣的一種菜。
馬各喜歡磯釣,休假時常帶兩個孩子南南北北去釣魚,還寫了一本書叫《偕子同釣》,讀著讀著覺得有這樣的爸爸真好!心裡也想著,未來希望自己也能成為這樣的父親,但至今好像一直沒有做到。
有一天,他又約我去他家吃飯,說報社有一個「特約撰述」的計畫,就是每個月給年輕作家五千塊的生活津貼,唯一的條件是把每一篇作品「優先」交給《聯合副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約束。
當時我雇員的月薪大約才四千塊左右,這樣的額外津貼和近乎沒條件的條件對我來說簡直是「不義之財」,馬各說服我接受,他的說法迄今難忘,他說:報紙是靠「內容」賺錢的,而你們的作品就是內容!
這筆津貼我足足領了五年,從大一一直領到大學畢業第一次拿到編劇金馬獎之後才結束。
一九七七年,我得了聯合報文學獎的第二獎(首獎得主是我後來的同事小野)。馬各說,既然得獎了,就趁這個時候出第一本書吧,因為算一算篇數和字數也都夠了。他說既然大部分的作品都發表在《聯合副刊》,那就交給聯經出版社吧?
也許之前根本都還沒有出書的想法,他這麼一提我反而不知所措起來,因為我始終沒有跟他說過先前和王榮文先生的約定。
那時真是年輕啊,這種「兩難」的狀態竟然讓我憂煩焦慮到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下課後終於忍不住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直接跑到報社找馬各,話都還沒說眼淚就先流,馬各嚇了一跳,一直問什麼事,「生活還是工作出了問題嗎?」聽完我自己認為的「困境」之後,他笑了,說:「這種事交給大人來處理,好不好?小孩就好好念書、好好寫作就好,不要去煩惱這個!」
記得我是這樣回答他的:駱先生,我不是小孩啦,我二十六了。
幾天後,王榮文先生打電話給我,說馬各已經跟他說過這件事了,他說之前就說過了,那只是一個約定和期待啊!最後他說:「謝謝你還記得我們的約定,我們等你的下一本書,好嗎?」
那個晚上,我睡了一場久違的好覺,心裡甜甜地想著的是:怎麼我遇到的都是這麼好的人啊!
不久之後,封面乾淨、清爽的書出版了,好像也就在這前後,馬各先生離開《聯副》,調任《民生報》的副總編輯,而我則在一九七八年寫了第一個電影劇本,一九八○年進入中央電影公司,同樣做寫字的工作,只是寫的是劇本,不是小說。
這是跟這本書有關的一些點點滴滴。
如果你竟然這麼有耐心地看到這裡,請容許我多講一句話:
好像也只有在那麼單純而美好的年代裡才會有這麼一群長輩,他們扒鬆了泥土,開闢了一塊園地,讓不同的種子自在地落下、萌芽,他們殷勤澆灌、施肥,然後微笑地看著他們各自成長,長成他們各自喜歡的姿態。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